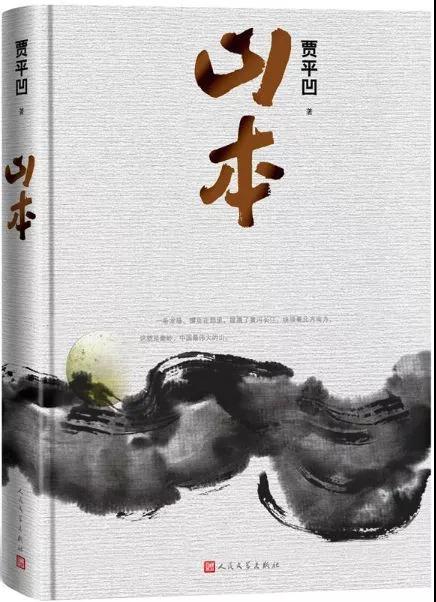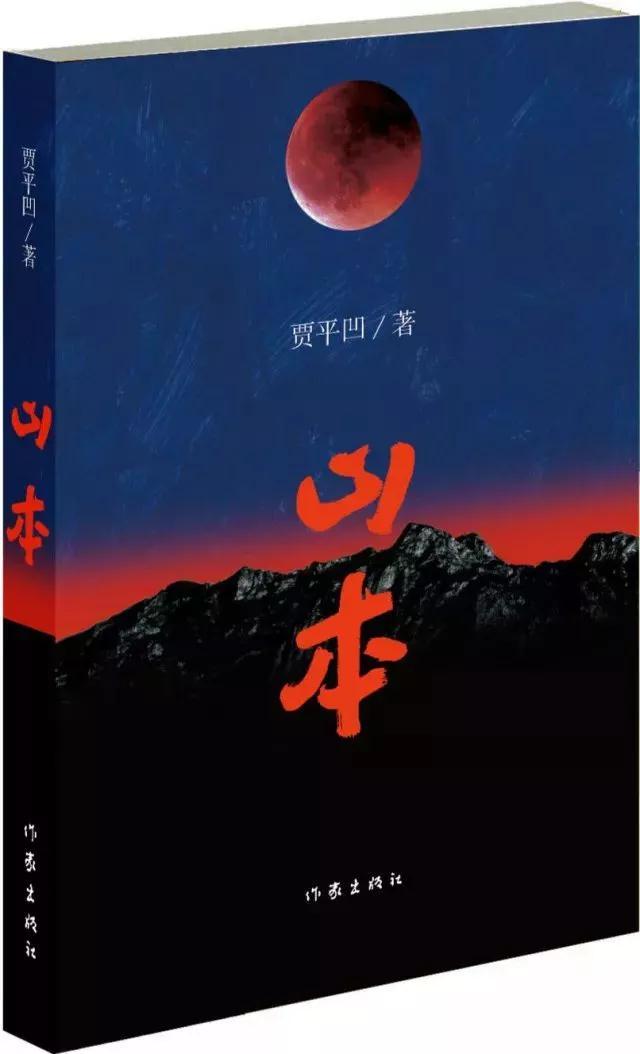對話嘉賓
賈平凹,1952年出生于陜西丹鳳縣棣花鎮,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1975年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西安市文聯主席、《延河》《美文》雜志主編。出版作品有《賈平凹文集》24卷,代表作有《廢都》《秦腔》《古爐》《高興》《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長篇小說16部。中短篇小說《黑氏》《美穴地》《五魁》及散文《丑石》《商州三錄》《天氣》等。作品曾獲得國家級文學獎五次,即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散文(集)獎。另獲“華語傳媒文學大獎”“施耐庵文學獎”老舍文學獎”“冰心散文獎”“朱自清散文獎”““當代文學獎”“人民文學獎”等50余次。并獲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法國“費米娜文學獎”,香港“紅樓夢·世界華人長篇小說獎”,北京大學“王默人·周安儀世界華文文學獎”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作品被翻譯出版英、法、瑞典、意、西、德、俄、日、韓、越文等30余種。被改編電影、電視、話劇、戲劇20余種。賈平凹是我國當代文壇屈指可數的文學大家和文學奇才,是一位當代中國最具叛逆性、最富創造精神和廣泛影響的具有世界意義的作家,也是當代中國可以進入中國和世界文學史冊的為數不多的著名文學家之一。
王雪瑛 評論家,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協會員、上海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第九屆全國文代會代表、上海報業集團高級編輯。2014年5月獲全國第六屆冰心散文優秀作品獎。著有《千萬個美妙之聲——作家的個體創作與文學史的建構》評論集,《傾聽思想的花開》、《訪問迷宮》、《淑女的光芒》等作品集。
聲音在崖上撞響才回蕩于峽谷
文 | 賈平凹 王雪瑛
王雪瑛
渦鎮不大,它僅是秦嶺中的一個點,渦鎮又很大,不僅是秦嶺中最大的鎮,主要是在閱讀中感到了渦鎮氣場的強大。《山本》是讓我們在渦鎮中感悟天地人之間的關系?天,白天黑夜的更替,斗轉星移的輪轉,這是天道對人的影響;地,莽莽蒼蒼的秦嶺,千山萬壑中無數生靈的繁衍生息;人,渦鎮內外的人與人之間愛恨情仇的纏繞,禍福相依的命運之間的交織。
賈平凹
渦鎮是秦嶺中的一個點,秦嶺又是中國的,人間的。我曾經畫過一幅畫:天上的云和地下的水是一樣的紋狀,云里有鳥,水里有魚,鳥飛下來到水里就變成魚,魚離開水躍入云里又變成鳥。人在天地之中。人之所以不能變成鳥與魚般的飛翔騰躍,是靈魂受困于物欲追求,而為了滿足自我的需求去掙扎、恐懼、爭斗。人類能綿延下來,憑的是神和愛,神,是人對于天地萬物關系的理解;愛,是人與人關系的理解。
王雪瑛
《山本》不僅僅沐浴著秦嶺的自然氣息,還浸透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血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你受到哪種文化或思想的影響最大?在《山本》中氤氳著莊子的氣息?
賈平凹
我一直好愛著佛和道,談不上什么研究,只是讀過一些經典,甚至參照著新舊約全書和古蘭經讀。要說最受影響的,那是《易經》和莊子了。因為受其影響,其思維和意識就不免滲到寫作中,這應該是我認識事物的另一個維度,而不是生硬強加的,不是要什么裝神弄鬼,它是自然而然的。
王雪瑛
是心靈受到佛和道的影響。在各種勢力的角逐中,麻縣長在任上難以作為,于是,他留意草木蟲鳥,采集多種標本,編撰了兩本大書,一本是秦嶺的植物志,一本是秦嶺的動物志。而你撰寫的秦嶺志:《山本》,主體是渦鎮的人物,時代的激流沖刷著人物命運的起伏跌宕,你和小說中虛構的人物麻縣長,一個是真實的作家,一個是虛構的人物,各自完成著秦嶺志,我感到一種真實與虛構相互呼應和勾連的方式,你寫作的時候,有過這樣的考慮嗎?
賈平凹
作家寫任何作品其實都是在寫自己。寫自己的焦慮、恐懼、懦弱、痛苦和無奈,又極力尋找一種出口。這樣,就可能出現真實與虛構的呼應和勾連。就以書中的人物來說,說穿了,常常是以人的不同面形成一組形象,比如周一山、杜魯成、井宗秀,就是一個井宗秀;陸菊人、花生,就是一個陸菊人。這一切在寫作中僅僅是混沌的意識,就讓它們自然發枝生葉。我強調自然生成,不要觀念強行插入,這如土地是藏污納垢,但它讓萬物各具形態的肆意蓬勃。
王雪瑛
“渦鎮之所以叫渦鎮,是黑河與白河在鎮子南頭外交匯了,那段褐色的巖岸下就有了一個渦潭……接著如磨盤在推動,旋轉得越來越急,呼呼地響,能把什么都吸進去翻騰攪拌似的。”你筆下的渦鎮,既是水文地理的寫實,也是人物命運的隱喻?比如麻縣長的自殺,他跳入河水中,最后卷入漩渦,阮天寶父母的慘死是因為兒子與井宗秀為敵,株連到他們……在亂世中,人如在激流中飄蕩,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麻縣長這個人物意味深長,他記下的草木在秦嶺歲歲年年地生長著,而他的生命消失在歷史的漩渦中……
賈平凹
時代、社會、世事都是漩渦,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被攪進去。這就是人生的無常和生活的悲涼。但在這種無常和悲涼中,人怎樣活著,活得飽滿而有意義,是一直的叩問。
王雪瑛
《山本》展開的情節和故事,是以秦嶺以及陜西二三十年代的民國史為背景的,讀完全書,感覺到你似乎沒有興趣總結那段歷史中各路人馬的成敗得失,不是梳理歷史大事件,而是描述世俗煙火中各自展開的日常人生,思索處于時代激流中的人物命運:個體的渴望與困頓,理性與情感,人性的復雜與黑暗,彼此的爭斗與殘殺……秦嶺不僅僅是《山本》的地域背景,而是你呈現與思索中最重要的價值尺度,秦嶺蘊含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恒長不變的價值能量,你依靠著秦嶺,審視和思索歷史、人性和命運?
賈平凹
你的提問已經回答了,回答得十分精彩。歷史是歷史,小說是小說,它們攫取的素材和處理素材是不一樣的。小說中當然有作家的觀念,但更大力氣的是在呈現事實,也就是它的人物,它的情節,它的語言,不管你這個時期,這個觀念去解釋它,還是那個時期,那個觀念去解釋它,它始終都在那里。這如有詩說,你走進花園,花開了,你沒走進花園,花也開著。小說家的工作是讓花開,在這一點上,我一直向往做得好些,但我還做得不好。
王雪瑛
有評論認為,這是你寫得最殘酷的一本書。《山本》寫出了農民和下層民眾參與的各種武裝力量之間的暴行,殘暴的復仇方式,被剝了人皮做鼓的三貓,被開膛剜心的邢瞎子……太多百姓死于無辜。面對你生活著的秦嶺上,曾經有過的殘殺與暴行,人性中的黑暗與殘酷,你的選擇是呈現和審視,而不是遺忘與掩飾,你有過猶豫嗎?在寫作的過程中,有著沉重的心理體驗嗎?在你痛心的反思中,流露的是深刻的悲憫?
賈平凹
《山本》中隨時有槍聲和死亡,因為這是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之所以人死得那么不壯烈,毫無意義,包括英雄井宗秀和井宗丞,就是要呈現生命的脆弱,審視人性中的黑暗和殘酷。越是寫得平淡,寫得無所謂,我心里也越是顫栗、悲號和詛咒。
《山本》人民文學出版社·精裝版
王雪瑛
在殘殺與爭斗中,生命在瞬間被毀滅,意義和價值被消解,是最讓人痛心的。你是一個有著豐富寫作經驗的作家,你判斷一部長篇小說的成功,主要依據是什么?在《山本》的創作中,讓你感到特別滿意的是什么,感覺還有遺憾的是什么?最難處理的又是什么?
賈平凹
年輕時閱讀,好技巧,好那些精美的句子,年紀大了,閱讀看作品的格局和識見。現在人閱讀習慣于看作品講了個什么故事,揭露了什么,宣傳了什么主義,或者有趣不有趣,其實人類最初談小說,就是為了自己怎么活人,里邊有多少值得學習的生活智慧。《山本》是我60多歲后的作品,我除了要講一個完整有趣的故事,就是一有機會就寫進了我60多年的生命經歷中所感知和領會的一些東西。遺憾的是這一點常常被閱讀者忽略。
《山本》中你能感覺某一章,某一節寫得特別痛快淋漓,那就是我得意時,而某一章,某一節寫得生澀遲滯,那就是我思路不暢或我不熟悉或不愿寫又不能不這么過渡時。生活中最難處理的是個人與社會的集體的人之間的關系,作品寫生活,也就是寫人的關系,也是最難的。
王雪瑛
《山本》的結構方式很獨特,全書不分章節,不設標題,僅以空行表示敘事的節奏,內容的轉換,請說說為什么采用這樣的結構方式?“陸菊人怎么能想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帶來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渦鎮的世事全變了。”這十三年指的是哪個時間段?
賈平凹
從《廢都》始,除了《帶燈》和《古爐》,別的作品,尤其是《秦腔》和《山本》我都采用這種結構方式,這主要是作品都寫日常生活的,想寫出日常生活的瑣碎和冗亂。黃河就是這么流的,大水走泥,少有浪花,全是在涌,遠望是一動不動,流下面全是激礪,而我們的日子更是這樣,好像這一天做了許多事,又像什么都沒有做,不知不覺天黑下來,這樣的一天就過去了。
這樣的寫法是比較難寫的,需要有細節而產生真實感和趣味性,又要保持住節奏。節奏在寫作中是極其重要的。至于問到十三年,那當然是指陸菊人當童養媳那一年到渦鎮全被毀掉這一年的之間。
王雪瑛
井宗秀是渦鎮的核心人物,也是《山本》中著墨最多,形象最鮮明的人物,“井掌柜是從來不說一句硬話,從來不做一件軟事。”這話,讓我過目難忘,這可以概括井宗秀的個性與為人嗎?
賈平凹
嘿嘿,這話是多年前陜西一位學者來說我的話,這話也可能是陜西的一句老話,我寫井宗秀時用上了。井宗秀在我心目中應該是戲劇里的小生角色。戲臺上的小生面白,不掛胡子,發聲也與眾不同。這種人是陰陽雌雄同體的,最能代表中國人的傳統審美。
王雪瑛
井宗秀,有著鮮明的個性和豐富的內涵,小說以他與渦鎮的關系來展開他的人生。渦鎮是他生命的家園,他與渦鎮是彼此塑造的關系,他兢兢業業地守衛著渦鎮,但他又因為報仇和殘殺給渦鎮招來殺身之禍,渦鎮失去了長久的堅固,最后毀于紅軍的炮火。他又在毀壞著渦鎮?也許,渦鎮在時代的風云中,在歷史的漩渦中,誰也無法一定守住渦鎮,因為一切都在動蕩中?
賈平凹
有晴天就有陰天,太陽和風雨是日子的內容。不是有句老話:淹死的都是會水的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么。那個年代的“英雄隨草長,陰謀遍地霾”。如果井宗秀算是一個英雄,那是如夏日的白雨,呼嘯而來,呼嘯而止。
王雪瑛
井宗秀和井宗丞是井家兩兄弟,他們是兩種不同的人生選擇,從地域上看,是固守渦鎮和離開渦鎮。在小說中的陳先生看來,他們都稱得上英雄,相對而言你對井宗秀用筆更多,刻畫得更全面而豐滿,請你說說井宗丞,他與井宗秀有什么不同?你在塑造他的時候,有怎樣的構想?
賈平凹
他們是同而不同,不同而同,是一棵樹上的左右枝股,是胳膊被打斷了骨頭還連著筋。人生常常這樣,要么需要不停地尋找對手,要么不停地尋找鏡子。《山本》在處理這兩個人的興趣在于人性的復雜,不關乎黑白判斷。
王雪瑛
《山本》呈現了在戰亂頻繁的動蕩年代,仇恨點燃著以暴制暴,底層百姓的旦夕禍福。你,以冷峻的筆觸揭示了“恨”,改寫著人的命運,你也細致地敘寫著“愛”,是一種強大的能量,會改變人物的命運,比如陸菊人和井宗秀的關系。
賈平凹
我喜歡陸菊人和井宗秀的這種關系,既和諧,又矛盾,他們被虛妄的東西所鼓動,從此有了向往和雄心,而相互關注著,幫扶著,精神寄托著,最后分離。一提到愛,現在的人多想到性愛,而人間卻是有大愛存在。
王雪瑛
在《山本》中沒有演繹酣暢淋漓的愛情,你筆下的陸菊人與井宗秀的感情,深長、獨特而節制。在亂世與困境中,他們彼此相互成就,是生命中的不可或缺,但他們又始終保持著距離。有人認為,他們的感情是傳統的“發乎情止乎禮”,有人質疑在現實人生中是否有這樣的感情?我想,這是不是有著豐富人生閱歷的你,對兩性情感的一種期許,一種理想?
賈平凹
還是談這種“愛”吧,有人說,陸菊人和井宗秀怎能不發生肉體的關系呢,我說,在那個年代,從小都一塊長大,發生身體關系是可能的,也是不可能的,而對于他倆來說,相互欣賞,又被要干大事的欲望鼓動,應該是不會發生身體關系的。作為男人,我讓井宗秀下部受傷了,作為女人,我給陸菊人身邊安排了花生,花生是代表了陸菊人的另一種欲望。
《山本》作家出版社·簡裝版
王雪瑛
閱讀中感覺你的細致安排,你在書寫和探尋一種更理性的情感,不是本能的強烈,而是克制的長久,是成熟心靈中生長的“愛”,歷經現實的磨礪,歷經戰火的考驗,依然留存在彼此的人生中。小說以他們的愛,在探尋愛的持久與能量?陸菊人的愛,不是易損的激情,而是將利他放在首位,成就對方,支持對方,這很不容易。渦鎮內外炮火與殘殺中的人性很暗沉,而他們的情感中透出了理想之光,人性之光?
賈平凹
是呀,你說得很對。
王雪瑛
井宗秀是一個有著理想的亮度,現實的灰度的形象,他有著英勇無畏的明亮,也有著殘忍腹黑的灰暗。而陸菊人是透著人性光亮的理想形象,她,與你以往小說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同,她是血腥的亂世中一株身姿挺拔又柔韌的野菊,她是偉岸的秦嶺孕育的秀外慧中的女子。他們隨著小說情節的展開成長著。井宗秀將原本屬于她的胭脂地里挖出的銅鏡送給了她,你這樣的情節安排大有深意?她的目光注視著渦鎮和井宗秀,她是一地碎瓷的年代里,沒有碎裂的銅鏡。
賈平凹
在我以往的小說中,人物一出場都是定性的,《山本》的陸菊人和井宗秀卻一直在成長。曾經寫過許多女性形象,應該說陸菊人是特別的,她并不美艷,卻端莊大方,主見肯定,精明能干,這是中國社會中男人心中最理想的形象,現實生活中常見到這樣的女人。她的原型有陜西清末時期很有名的周瑩的部分,更有我家族中三嬸的部分。胭脂地里挖出的銅鏡,是我寫作中的靈光一現,那時就想到她該是井宗秀的鏡子,該是渦鎮的鏡子。
王雪瑛
你在后記中有言,在寫作《山本》時,你的書房里掛著“現代性,傳統性,民間性”的條幅。我想,小說寫的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秦嶺渦鎮民間的往事,行文中氤氳著傳統文化的氛圍,而你認識和審視的目光是現代的,你以現在的思想來認識歷史上權力爭斗的真相,人性深處的復雜,個體命運的難測?
賈平凹
現在寫小說,沒有現代性那怎么寫?現代性不僅是寫法,更是對所寫內容的認識。傳統性,我主張寫法上的中國式敘述。民間性,往往是推動現代性和傳統性,它有一種原生的野蠻的卻有活力的東西。
王雪瑛
你原來想寫一部秦嶺的散文體草木記動物記,而最終寫成的是一部視域宏闊內蘊豐厚的小說。一面是以“賈氏日常生活現實主義敘寫法”,讓讀者看見“一堆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另一面又以靈動而神秘的描摹,展開秦嶺的自然生態,動物與植物的傳神細節,寬展師傅的尺八,陸菊人家里的貓,有龍脈的胭脂地,老皂角樹的焚毀,鐘樓里的尖頭木楔,炮火中紛飛的鳥群,天空中火紅的云紋,讓讀者感受到了萬物有靈的意蘊空間。既有日常的寫實,又有神秘的迷離,是《山本》的小說美學?也是你對人世間,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解?
賈平凹
把握一個故事,需要多種維度、空間才可能使故事活泛,讓人感覺到它一切都是真的,又是混沌的產生多種含義。故事的線條太清晰,會使人感覺這是編造的一個故事,移栽樹木,根部不能在水里涮得太干凈,連著土一塊移栽了樹才能活。
王雪瑛
《山本》中有兩組人物,一組是與以井宗秀為主的渦鎮預備團(后升級為預備旅)、以井宗丞為主的秦嶺游擊隊,以阮天保為主的保安隊,他們在渦鎮內外不停地爭斗著,構成了推動情節的緊張關系。還有一組人物,是由陸菊人、目盲的陳先生和失聰的寬展師父組成。陳先生在安仁堂,為渦鎮的人們療治著身體的病痛,也為亂世中眾生開啟心智。寬展師父的悠悠尺八和誦經,給身處現實困苦中的渦鎮人,帶來悲憫和超度。陸菊人是這兩組人物的紐帶,她是渦鎮亂世中的銅鏡,她體驗著,承受著紛繁日子中的冷暖悲歡……她的目光中有著你的注視,她的無奈中有著你的心事,她的仁愛與憐憫中有著你的情感溫度,塑造他們的時候,流露著你的價值尺度?
賈平凹
你全都說了呀,社會是一個網,生活是一個網,寫作中作者是一個蜘蛛吧。
王雪瑛
在一天中,你習慣于在哪一個時間段寫作?在《山本》的寫作中,最順利的時候,一天寫了多少字?海明威說,在知道接下去會發生什么的時候停筆,第二天就能順利地接著寫下去。你的寫作習慣是怎樣的呢?
賈平凹
我現在沒有整塊時間呀,會多活動多,我基本上是有事忙事,沒事了就抓緊寫。如果這一天沒有事,我從早上8點30分可以寫到11點,下午3點可以寫到5點,這樣能寫5000字左右。海明威的經驗是作家的普遍做法,就是這一天寫順了,萬不能一氣寫完,應是第二天接著寫,而不至于寫不下去。我通常是每天早晨起來,要在床邊坐那么一個小時,想今天要寫的內容,不說話,不吃不喝,不允許家人打擾。
王雪瑛
你以這樣的方式在心中孕育文思。評論家陳思和對你貫穿當代文學近40年創作,有過高度的評價:賈平凹既能夠繼承五四新文學對國民性的批判精神,對傳統遺留下來的消極文化因素,尤其是體現在中國農民身上的粗鄙文化心理,給以深刻的揭露與刻畫;然而在文學語言的審美表現上,他又極大地展現了中國本土文化的力量所在。他在新世紀以來創作的《秦腔》等一系列長篇小說的藝術風格,都是帶有原創性的,本土的,具有中國民族審美精神與中國氣派。你對這樣的評價怎么看?
賈平凹
陳先生是我敬重的大評論家,他的評論文章不是很多,但每有文章,必有重要觀點,對文學的影響甚大。他對我的一些評論,給過我相當大的力量。評論和文學創作是共生的,相互影響,發酵、刺激和作用的,光照過去再反射過來,聲音在崖上撞響才回蕩于峽谷。
(原文刊發于《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4期)